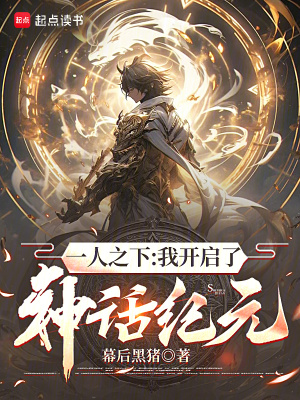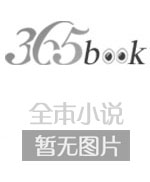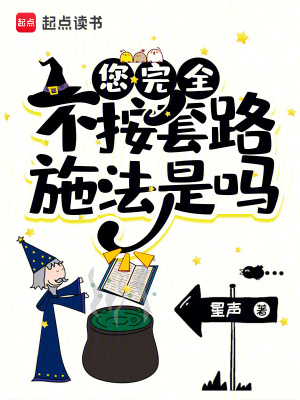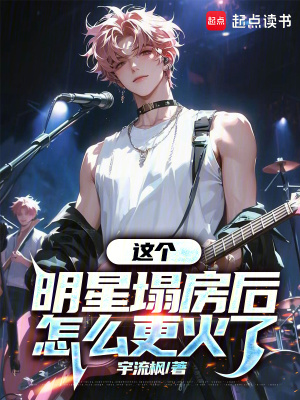王庭相就不以为然,曾说裕王该学的是帝王之道,而不是工匠之术。
自从投到墨家门下后,王庭相就是墨学的负责人,蒋庆之这等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的胸襟,令王庭相暗自佩服。
对有大才的人,就得敞开、敞亮了用……蒋庆之当时和反对这个决定的徐渭等人说:“越是倨傲之人,越是喜欢端着架子。我用王庭相负责墨学,便是把他架在了架子上。他不会下来。”
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这个味儿。
自从执掌墨学后,王庭相堪称尽职尽责,蒋庆之给他的待遇颇为优渥,可徐渭每次见到王庭相穿着很是朴素,有一次便忍不住问了为何。
王庭相不答,徐渭去打听了一番,得知王庭相每月的俸禄大半都用于资助学生。
城外墨学最早一批学生出身贫寒,家里不说揭不开锅,但也就是能勉强果腹而已。
有的学生家中三餐难继,幸而墨学免费供应两餐。王庭相有次接到举报,说几个学生偷藏食物。
王庭相大怒,便把几个学生叫来。
一番问话,王庭相这才得知,这几个学生家中艰难,自家在墨学能吃饱喝足,想到家中父母兄妹饥肠辘辘,便忍不住拿了些食物藏着,带回家去给家人吃。
墨学的食堂没有数量限制,只要你能吃,就可以无限制去打饭菜。
几个学生利用了这个规矩,一次藏一些,食堂打饭的人发现了猫腻,便禀告了上去。
王庭相拿着棍子抽了几个学生一顿,每人给了一百钱,让他们带回家去。
从那时开始,王庭相每月的俸禄都会拿出大半来资助墨学中的贫困学生。
“咱很是好奇,长威伯明明可以自家掏腰包资助那些学生,如此也能得个好名声,为何让王先生私下资助呢?”
裕王去学习,杨锡没事儿,正好遇到周夏,便问了此事。
当时裕王得知此事后,只是叹息了一阵子。
周夏负责墨家基地,每日事儿多如牛毛。好不容易得了空闲,坐在墙根那里乘凉。他懒洋洋的道:“老师说过,救急不救穷。每月都给,看似仁慈好心,可却会助长那些人的惰性。另外让王先生私下资助不是坏事儿。”
“啧!救急不救穷……也是。”杨锡觉得这事儿还真是如此,“让王先生资助为何不是坏事儿?”
周夏突然有些怀念老师的药烟,他曾抽过一次,觉得味儿……怎么说呢!古怪,但印象深刻。
“一个人倾注于某件事上的心血越多,就越会不舍。”
杨锡一怔。
“长威伯这是想留住王先生?”
“留不是问题,是用人之法。”周夏跟着老师耳闻目染,学到了许多,“墨学乃是我墨家和老师的根基,执掌墨学之人,必须要倾尽全力,尽心尽力。
老师曾说,让一个人一年两年尽心尽力不难,难的是长久如此。所以,最好的法子便是让墨学成为王先生的心血所系。”
蒋庆之当时说的是:让墨学成为王庭相的事业和一生追求。
后世用人之法最高明的不是报酬优渥,而是把工作变成员工的事业和追求。
“周夏。”
正说到王庭相,这人就来了,急匆匆的过来说,“今日工课改成下午可好?”
墨学有工课,也就是实践课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工坊就是他们的课堂。
周夏起身,“为何改期?”
工坊已经做好了准备,你学堂改期这不是放鸽子吗?
王庭相眉间有怒色,“有学生的家人来了,问学生毕业后是否要进工坊做事,老夫问这话谁说的,说是外面都在说。”
杨锡觉得这事儿有些诡异。
朝中才将反对墨家基地从工部抽调工匠,这外面就开始传谣。
别小看这个谣言,对于那些学生家长来说,宁可让自己的子弟去种地,去经商,就是不肯做工匠。
一旦做了工匠,弄不好就会成为匠户。
大明户籍制度很操蛋,一人是匠户,他的儿孙都是匠户。
匠户也就罢了,每月特喵的还得免费自带干粮去给官家干活……类似于劳役的性质。
谁愿意干?
所谓士农工商,这是四民尊卑顺序。可实际上除去士之外,其他三等人早已换位了。
读书人第一,商人第二,农户第三,最后才是匠户。
当然,还有最差的军户。
也就是武人。
所以一听到这等传言,那些家长便坐不住了。
周夏蹙眉,“这风来的不是时候。”
王庭相说:“老夫不是那等坐井观天的书生,长威伯南下清洗了松江府和南直隶,引得京师震动。那些人是想借此来打击长威伯。围魏救赵的把戏罢了。不过那些学生如今人心浮动,这事儿得给他们一个准信。”
他看着周夏,“要不,快马令人请示长威伯?”
周夏摇头,态度很坚定的道:“老师对当下的户籍极为不满,说前唐府兵制便是前车之鉴。王先生可去告知那些学生家人,这些弟子,不会成为匠户!”
王庭相眉心舒展,“如此老夫就有数了。对了,外面还有传言,说我墨家缺乏工匠,和工部打擂台无果,便打那些学生的主意,这才引发了此次纠纷。”
“这是有预谋的。”周夏淡淡的道:“王先生放心,最多半月后,咱们一批新工匠就能出师了。”
“好!”
王庭相风风火火的走了。
杨锡啧的一声,“围魏救赵吗?”
周夏冷笑道:“老师早就说过,靠山山倒,靠人人跑。墨家要发展壮大,苦练内功才是王道。至于外力,不可为倚仗。”
杨锡琢磨着这番话,等裕王今日的学习结束后,他跟着一起回宫。
“看你磨皮擦痒的,有事就说。”裕王没好气的道。
“这事儿吧……”杨锡把今日自己的见闻告知了裕王,最后说:“奴婢觉着长威伯用人之道颇为微妙。”
他没敢问的是:这等用人之道,长威伯可曾教授给殿下?
这话有挑拨离间的嫌疑。
裕王一怔。
回宫吃了午饭,长乐来寻裕王,说是给道爷送早饭。
道爷的作息时间颠倒,别人吃了午饭他才起床。
“也好。”
裕王和妹子一路去了西苑。
“三哥,表叔何时回京?”
长乐提着食盒问。
裕王被正午的太阳晒的有些发昏,懒洋洋的道:“大概秋季吧!”
他若是知晓表叔此刻正在大海上浪,大概会改口说大约在冬季。
“哎!”
裕王有些羡慕长乐,“如今你在宫中无人敢惹,父皇又宠你,还有什么值当你叹气的?”
长乐说:“上次我去新安巷,大鹏都会叫爹娘了,可娘在爹不在。”
“大鹏可好玩?”裕王觉得长乐有表叔口中女文青的倾向,多愁善感了些,便转了个话题。
“好玩。”长乐数着大鹏如何如何好玩,又埋怨两个兄长还不成亲,也好生几个孩子给自己玩。
“还得一两年。”裕王也有些憧憬自己未来的妻子。
到了永寿宫,道爷早已起了,正和几个臣子商议事儿。
长乐乖巧的说去转转,裕王隔着一扇门旁听,这也算是观政。
道爷一袭道袍,看着越发的清瘦了,和最近开始变胖的老元辅对比鲜明。
严嵩,朱希忠,崔元,徐阶,五部尚书。
“长威伯上了奏疏,让朝中派遣工匠南下,说什么开工坊。臣不解,这朝中开工坊也就罢了,为何要去南方?”
严嵩说话的速度不快不慢,说到关键处时速度更慢,仿佛在斟词酌句,“墨家城外工坊也在索要工匠,两边加起来索要的工匠数目让工部很是为难……”
“做不到。”崔元补刀,“工部正好在。”
工部尚书姜华有些纠结,“是差了不少人。”
严嵩颔首,继续说道:“此事倒是让工部为难了。”
这话在暗指工部姜华支持蒋庆之,为此不惜削弱工部的实力。
姜华眼皮跳了一下,却没反驳。
严嵩说:“如此,臣以为,长威伯索要工匠之事,当批回。不许。”
说完,他垂眸等着道爷的决断。
这事儿姜华这个当事人都默认了,朱希忠也不好开口。
道爷想到了蒋庆之先到一步的书信,在书信中,蒋庆之阐述了自己对未来海贸和南方工商业发展的思路。
——不能让南方坐大!
道爷总结了一番,就这么一句话。
一旦出海贸易,以南方的工商业规模,全力以赴的话,不出五年,南方经济将会迎来一个巨大的飞跃。
而后呢?
“你等说说,人有了钱,有了巨量的钱之后,还会追求些什么?”
道爷突然问了这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。
重臣们默然。
门外,裕王说:“父皇,会追求权力。”
不愧是朕的儿子,这哏捧的好。
严嵩干咳一声,“陛下,可工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”
没人!
拿什么给蒋庆之?
其实不是没人,不过朝中也有许多工程要做,总不能停下那些事儿吧?
蒋庆之南下后大杀四方,势头太盛,若是再强行索要工匠,树敌太多。
道爷眯着眼,“此事……”
“父皇。”
道爷刚想点头,闻言问:“何事?”
裕王在门后说:“这工匠之事,无需工部操心。”
众人:“……”
“殿下这话能准?”崔元看似好心的提醒。
“自然准。”裕王自信的道:“我方从城外归来,墨家工坊中,不缺工匠!”
周夏说半月,但裕王知晓,别说是半月,就算是半年,在朝中反对的大势之下,墨家和蒋庆之绝不会低头。
“另外,周夏说了,此后各自安好。”
我不要你的工匠,对不住,回头您也别开口。
咱们,就此分家!
卧槽!
严嵩一怔,崔元却笑了笑,“周夏年轻气盛,可能做主?”
裕王坚定的道:“此事,我可担保!”